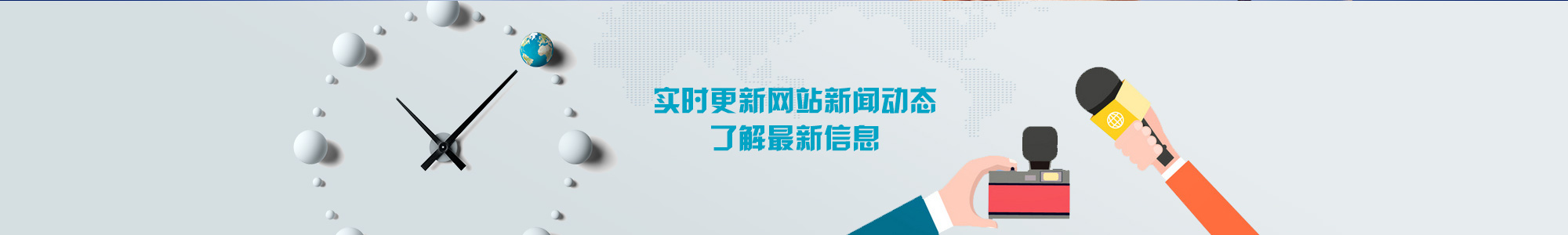张忠培是一个好老师。我从1981年入学开始认识张先生,最初的印象是从课堂开始的,后来又跟他读硕士、读博士,不断地、逐渐地感受到了他作为老师、作为先生的师者魅力。在本、硕、博三个阶段的学习过程中,张先生的教学方法是不一样的。本科生阶段听他的课,完全是以“教”为主,把传授知识和培养兴趣当做重点,体现出的是耐心和包容。他授课逻辑清晰,自成体系,许多问题都有自己的见解,多数结论都有确凿的证据。虽然我当时并不知道什么样的老师才是大学的好老师,但是我已经朦胧地感觉到:张忠培是一个有科研功底和成果支撑的人,将来跟他学习,估计能有出息。1985年本科毕业后,我如愿以偿地成为了他的研究生,1988年硕士研究生毕业留校工作了12年以后,我又以教授的身份考上了他的在职博士研究生。硕、博阶段的学习,先生以“导”为主,以“教”为辅。为我选定的学位论文,要么是难题,要么是大题。尽管很害怕、很恐惧,但没有任何商量和讨价还价的余地。整个过程中,体现的是他“教”我“学”、我“研”他“导”,追求的是“导师尽职尽责、学生尽心尽力、论文尽善尽美”。为了鼓励我完成硕士论文,他不止一次地跟我说“要想当一流学者,就必须敢选大题目,敢做大文章,敢在大问题上争取发言权。”为了完成他亲自为我指定的超大博士论文题目,我不得不辞去身上的行政职务,把全部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论文的写作当中。1988年6月,当我的硕士论文《半坡文化研究》得到答辩委员会苏秉琦、严文明、黄景略、李伯谦等学术大师和一流学者表扬的时候,我才真正意识到先生通过启发思考、深化理论、提升境界、追求高远的训练,培养了我知难而上、勇于拼搏、敢打硬仗的信心和勇气。2005年12月,当我的博士论文《中国东北地区夏至战国时期的考古学文化研究》顺利通过答辩,并相继获得吉林大学、吉林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一等奖和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提名奖的时候,我才真正明白了先生对我的良苦用心和远期厚望,明白了老师是在用大题目助我成长、推我前行,用高难度的选题锤炼我意志、开发我潜能、培养我信心、指引我前程。本、硕、博三个阶段的学习,让我从先生的身上我看到了什么是“大师”的胸怀和谋略,领略了什么是“大家”的气度和风范。让我知道了能够以自己的学术体系支撑本科教学,能够通过科研训练帮助研究生掌握科研方法,能够通过论文选题为学生凝练出受用一生且具有很大发展潜力的研究方向或研究领域的老师,才是真正的“好老师”。
张忠培是一个好学者。他一生笔耕不辍,著作等身。留下的著述,篇幅之多、质量之高、文字量之大,令人叹服。科研成果上,他是一个用圆珠笔写字,比别人用电脑打字还快的学者,说明他是何等的勤奋。学术会议上,他是一个不用PPT也能把自己的观点和思想表达清楚的大家。他一生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主张“被考古材料牵着鼻子走”,“有一份材料说一分话”。追求“以物论史、透物见人,替死人说话,把死人说活”的治学之道。他从陕西华渭地区起家,逐步地把研究视野扩展到了全国。他从考古学上的新石器时代着眼,逐渐地把研究领域下延到了夏商周时期。他从大量的考古学个案分析入手,渐渐地走上了方法论和学术史的研究,实现了从实践探索到理论总结的升华和转变。从张忠培先生的学术生涯中,我最终总结出了这样一个道理,那就是“围绕着同一个问题查资料、看书、写文章是‘搞科研’,走从点到线到面的科研之路是‘做学问’,取得点、线、面之间具有内在联系的一系列科研成果的人才是“真学者”、“好学者”。
张忠培是一个好朋友。他是一个可以交心的人,和他谈话,不用藏着掖着,也不用拐弯抹角,完全可以开门见山、直奔主题,就像朋友一样。谈话中,他所关心的,永远是事业和学术问题,永远是人生观和价值观问题,很少涉及到房子、车子、票子、位子等一些生活琐事。他一生刚直不阿,铁骨铮铮,勇于坚持真理,敢于坚持原则。一生愿意与人相伴、与人为善,经常“骂人”、“训人”,但从不背后“整人”、“害人”。他是一个外冷内热、外严内慈、爱徒如子的人。作为学生,总是见则害怕,不见则想。可每次见面之后,又都会有一种老朋友、真朋友会晤的感受。他有说不完的话,永远是口无遮拦、言表己心、直言不讳。满满的,都是正能量。每每将要起身告别之前,他都依依不舍,总是以“再抽最后一支烟”、“再喝最后一杯茶”为借口加以挽留。不管什么时候,在先生面前,听到的永远都是激励、嘱托和教诲。人的一生,都有属于自己的秘密,一辈子不愿意告诉别人的秘密,可先生曾不止一次地对我说,他一生做的最错误的一件事就是离开了吉林大学,并要求我替他保守这个秘密。2012年初冬,当我已然决定调离吉林大学,到浙江大学工作的时候,我一直瞒着先生,可最后还是被他知道了。他不止一次地劝留我、告诫我,要我不要重走他的老路、错路。他说学校培养一个人才不容易,吉林大学的平台很好,一定要谨慎对待,千万不要做让自己后悔一生的蠢事、傻事。5年过去了,我在母校发展的很好,还算顺利。事实证明,时年78岁的张先生对我的劝告是及时的、正确的,所以,我一辈子都要感谢我的恩师、我的朋友。常言道,“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先生就是这样的人,每次见面聊天,都能获益匪浅,都能感受到他的睿智、深邃和高屋建瓴的大气。有人说,“一生得一知己,足矣”。我自认为,先生不仅是我的学术导师、也是我的人生知己,更是我生活中少有的贴心人、好朋友。
现如今,作为“好老师”、“好学者”、“好朋友”的张忠培先生走了,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大家的心情是一样的,都很难过,都很伤感。让我们化悲痛为力量,继承和发扬张忠培先生的办学理念、治学精神、育人思想,继续走以中原考古为基础、以边疆考古为特色、以外国考古为方向、以学科交叉为手段、以文物保护为己任的具有吉林大学鲜明特色的考古之路,团结一致向前看,撸起袖子加油干,用实际行动和新的成绩告慰先生、纪念先生,为早日把先生亲手创建的吉林大学考古学科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学科而共同努力!
(作者赵宾福 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
 星火不灭处,再寻白求恩09-22
星火不灭处,再寻白求恩09-22 吉林大学程妮娜教授等著《渤海国...09-22
吉林大学程妮娜教授等著《渤海国...09-22 吉林大学举行“鼎新学者”迎新暨...09-20
吉林大学举行“鼎新学者”迎新暨...09-20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设立20周年暨...09-20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设立20周年暨...09-20 郭孔辉:我与吉大汽车09-19
郭孔辉:我与吉大汽车09-19 吉林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蒋青...09-19
吉林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蒋青...09-19 张希会见中国工商银行党委委员、...09-18
张希会见中国工商银行党委委员、...09-18 破解衰老刻度,揭秘生命密码——...09-18
破解衰老刻度,揭秘生命密码——...09-18